原則的力量
2003年3月30,「凡事有個極限」(Yesh Gvul)的主席以夏.門努凊(Ishai Menuchin)因其所領導的拒絕服役運動,獲頒「羅米洛獎」(The Rothko Chapel Oscar Romero Award)。美國作家以及文化評論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受邀於頒獎典禮致詞。在講演中,她向若雪.柯利以及拒絕在佔領區服役的以色列士兵致敬,也向所有秉持良心、堅守原則的行動者致敬。在若雪逝世一週年的這一天,我們特將這篇講稿全文翻譯,做為我們的紀念。– 巴勒斯坦資訊網 2004.3.16
出處:Peretz Kidron ed., Refuselink: Israel’s Soldiers of Conscience (London: Zed Books, 2004)。
在無數英雄以及為數更多的受害者當中,讓我先舉兩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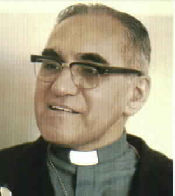
Oscar Arnulfo Romero
第一個是奧斯卡.羅米洛(Oscar Arnulfo Romero),聖薩爾瓦多的大主教。23年前,也就是 1980 年 3 月 24 日,他在教堂主持彌撒時被謀殺致死,因為他「勇於宣揚正義的和平,並且公開地反對暴力與壓迫的力量。」(引自羅米洛獎紀念頌詞)
第二個是若雪.柯利,來自美國華盛頓州奧林匹亞地區的一位 23 歲的大學生。她在 2003 年 3 月 16 日迦薩走廊南部的拉法地區(與埃及交界處)試圖阻止以色列軍隊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時,儘管身穿醒目的橘色反光外套,仍然被殺害。若雪是拉法地區 8 位來自英美的年輕人之一,她們自願在拉法當「人肉盾牌」志工。當她揮舞雙手,並透過麥克風向著迎面而來的武裝 D-9巨型推土機喊話時,壓土機沒有停止前進,而是將若雪輾了過去。

若雪和ISM伙伴們
這是兩位象徵性的人物。當他們犧牲自我在從事非武力、有原則、具有危險性的反抗行動時,他們被暴力與壓迫勢力所殺害。
我們都是受徵召者
讓我們先談風險。被處罰的風險。被孤立的風險。被傷害或殺害的風險。被鄙夷的風險。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受徵召者。對所有的人來說,僭位、表達異議、製造爭議以及冒犯大多數人的忠誠感,都是很艱難的。我們因此在正義、和平、和解等目標下結合,與更小的一群人一同示威、抗議、從事民事不服從行動。這一切不是為了耀武揚威,也不是為了血戰沙場。
如果排拒主流與堅持異議還沒有成為你的習慣或能帶給你滿足,由自己的部落脫隊進入另一個數量上更小、但思想上更廣的世界,將會是一個複雜、困難的過程。
要違背部落的智慧是困難的,尤其當這個部落永遠將自身成員價值置於一切之上。在這時,堅持他人與自身的同等價值只會惹人反感並被疑為不忠。
將自己的忠誠獻給我們知道的人、看得到的人、緊密與我們結合的人或分享生命的人,總是容易多了,因為我們是一個「恐懼共同體」(community of fear)。
我們不要低估我們所反對事物的力量,也不能低估勇於提出異議者所會受到的報復力量,尤其當他們所反抗的殘暴與壓迫是被多數人之恐懼所合理化的。
我們是肉身。我們會被刺刀穿透,會被自殺攻擊者撕裂,會被壓土機輾碎,在教堂中也會被開槍射殺。
恐懼使人們結合,也讓人離散。一個充滿勇氣的典範同樣可以激發社區,因為勇氣與恐懼同樣具有傳染性。但是勇氣,某些勇氣,也會使得勇者孤立。
原則的宿命就是,儘管人人都頌揚它,但當它會帶來不便時,宣告它的人們就會將之犧牲。一般而言,道德原則會與約定俗成的行為有所牴觸,故堅持道德原則往往會帶來不愉快的後果。背棄原則的人喜歡說:「我已經盡我所能了。」當然,這是指環境容許下的最大努力。
不、我不當兵
讓我們假設這原則是這樣的:壓迫與羞辱一整個民族,有系統地剝奪人們的居所與適當營養,破壞人們的居住環境與生計,不讓人們接受教育與醫療,阻止人們相互往來等,是不對的。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行為是各種因素所造成,但不管起因是什麼,這些行為都是不對的。
在我們的道德生活與道德想像中,我們有偉大的反抗典範,這就是那些說「不,不,我不服從」的人的偉大故事。
什麼典範,什麼故事?一個摩門教徒可以抵擋重婚罪。一個堅決反對墮胎的人可以抵制允許墮胎的法律。他們同樣可以引用宗教、信仰或道德上的宣稱來抵抗公民社會的律令。人們可以引用高於國家法律的更高權威來合理化各種罪行或是追求正義的高尚奮鬥。
勇氣本身並沒有道德價值,因為勇氣本身並不是一個道德上的美德。邪惡的歹徒、謀殺者、恐怖份子,都有可能很勇敢。要將勇氣形容為一種美德,我們需要在前面加一個形容詞:我們應該說「道德勇氣」,因為世界上也存在「不道德的」勇氣。「反抗」本身也沒有價值。反抗的內涵,決定了它的價值與它的道德必要性。
讓我們說:反抗非法戰爭。讓我們說:反抗佔領與兼併其他人民的土地。
再說一次:反抗於其內在並不具有優越性。反抗的正義性,在於反抗者以正義之名所反抗的事物。一個目標的正義性,與其所宣稱者的德行並不相干,也不會因之而提升。一個目標的正義性,最終將視人們所真實描述的事態,是否真的不正義或不必要。
以下是我在經歷過許多年的迷惘、無知與焦慮後,才逐漸認知到的真實事態。
以色列這個受過傷、充滿恐懼的國家,正經歷著其動盪歷史上的一個最大危機。這危機的根源來自其在1967年以阿戰爭勝利後於佔領區所採行的屯墾區興建政策。歷來的以色列政府持續控制約旦河西岸與迦薩地區,不讓巴勒斯坦人建國,這對兩方面的人民,都是一種道德、人性與政治上的災難。
巴勒斯坦人需要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以色列也需要一個有主權的巴勒斯坦國。我們在海外的人雖然希望以色列這個國家可以生存,但是這不能夠也不應該以不擇手段的方式來達成。
有許多充滿勇氣的以色列見證人、記者、建築師、詩人、小說家、教授等人,描述、紀錄、抗議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軍事佔領以及殘酷的對待方式。對於這些人,我們懷有一種特殊的感謝。
對於由以夏.門努凊(Ishai Menuchin),「凡事有個極限」(Yesh GvulThis is an external link)的主席所代表的一群拒絕在 1967年疆界外服役的勇敢以色列士兵,我們懷有最大的敬意。這些士兵知道所有的屯墾區最終必須撤離。

IShai Menuchin(以夏門努清)
這些猶太人士兵嚴肅看待了1945-46年紐倫堡大審所提出的原則,那就是,一個士兵沒有必要遵守不公正的命令,甚至有義務違抗違反戰爭公約的命令。
不服從的義務
這些拒絕在佔領區服役的以色列士兵並不是違抗某個命令。他們是拒絕進入佔領區,因為在那兒,他們必然得服從缺乏正當性的命令,必須執行一些勢將延續壓迫與羞辱巴勒斯坦人民的勤務。在佔領區,房子被拆除、農作物被連根拔除、市場攤販被堆土機壓平、文化中心被劫掠,還有現在幾乎每天都有不分年齡階層的平民被射殺。以色列佔領了超過英管巴勒斯坦22%的土地,她在這應該是日後巴勒斯坦國之土地上的殘酷暴行也是無庸置疑的。這些士兵與我同樣相信,以色列應該無條件地撤離佔領區。他們集體地表達了他們不願在1967年疆界以外的地區執勤以「控制、驅離、羞辱,並且斷絕整體人民的生計。」
這些拒絕服役士兵的行為–目前有1100名左右,其中超過250名已經入獄服刑–不正是告訴我們,儘管無法使以色列撤掉屯墾區,但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可以一起為和平努力的。這些英勇的少數人或許無法立即影響巴勒斯坦自治當局最需要的改革和民主化;他們的挺身而出,也無法鬆開捆綁以色列社會的宗教頑固與種族歧視,或是減少受屈辱的阿拉伯世界充滿敵意的反猶宣傳,或甚至是阻止自殺炸彈客。
但他們只是明白地宣告說,「夠了!凡事有個極限。」Yesh gvul(意即凡事有個極限;以色列士兵選擇性拒絕服役運動)他們建立了一種反抗的典範。一種不服從的榜樣。而這樣做,是會受到懲罰的。
我們不曾忍受過這些拒絕受徵召士兵所正承受的處罰,他們其中許多人已經入獄服刑。在這個時刻談論和平在美國只會被訕笑(譬如最近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發生的那樣)、被騷擾、或是被列入黑名單(例如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連鎖電台集團抵制狄克西女子合唱團);簡單地說,會被咒罵為不愛國。
在「我們站在同一陣線(United We Stand)」或「贏家通吃(Winner Takes All)」這樣的社會特質下,美國這個國家已經把愛國主義和輿論劃上等號。托克威爾(Tocqueville)這位至今仍是美國最透徹的觀察人,曾經提到新興美國之民眾的高度順從。175年後,他的觀察還是準確無誤。
當美國外交政策激進轉變時,美國高漲的國家狂熱輿論往往可以輕而易舉就可找到各種說辭來推銷這些政策是對美國有利的,還有對伊拉克這類戰爭也是必要的。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似乎相信,美國是有權力、甚至有責任來管理這個世界。
如果邪惡止不住怎麼辦?
我們通常在頌揚依據原則行事的人們時,總是說他們是終將獲得勝利的正義之戰的急先鋒。
但是,萬一不公義並沒有消失呢?如果這些邪惡是無法制止呢?我們知道,這些目標至少短期內是不可能的,而所謂的短期,其實可能還是指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非常尊敬這些拒絕在佔領區服役的士兵,就如同我強烈地相信他們的理念要經過很長久時間才會被社會接受。
但是,最讓我心中感到震撼的是,當人們知道依據原則行事並無法改變勢力的不均、階級的不平等、以及政府為了安全而非和平理由所執行的殘忍政策時,卻仍然願意堅守原則。
士兵之所以在那裡,是因為「我們」遭到攻擊或是受到威脅,卻不說是我們先攻擊他們的。現在對方已經開始反擊,造成了我們的傷亡。是他們違反了戰爭的「恰當」規範。是他們表現得像「野蠻人」一樣-這也是我們這個世界愛給那個世界的人的稱呼。而他們的「野蠻」與「非法」行為,不但帶給我們侵略的藉口,也給我們氣勢來打壓、箝制或是迫害那些反對政府這種侵略行為的公民。
我們不要低估我們所反對事物的力量。對幾乎所有的人來說,這個世界並不是我們所能掌控的。常識和自保的本能教導我們如何適應那些我們無法改變的事物。
我們不難想像我們當中的某些人,將如何被說服相信一場戰爭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尤其當這樣的一場戰爭儘管使用了超強攻擊火力,也被闡釋為促進和平及安全的小規模軍事行動或是解除武裝行動。而這樣的侵略行為,我們還大而皇之地稱為「解放」。
撇開國力、財富、軍力上的差距與人口的懸殊不說,有多少美國人知道伊拉克的人口數是兩千五百萬人,而其中半數是孩童?(美國人口數是兩億九千萬人。)在這樣的狀況下,不支持敵人炮火威脅下的我方士兵,仍然是叛國行為。
有可能在某些情況,這些威脅是真的。在這樣的狀況下,這些遵守道德原則的人就好比是跟著一輛行進中的列車旁奔跑叫喊著:「停下來!停下來!」。
火車會停嗎?不會,至少不是現在。火車上的其他人會跳下來並加入那些地面上的人嗎?或許有些人會,但大多數的人不會。(除非,他們面臨全新不同的恐懼。)
「根據原則行事」的劇本告訴我們,我們不必考慮依照原則行事是否是權宜之計,或者我們這樣做能否達成目標。根據原則行事本身就是好的。不過,這樣做也是一種政治行動。就某方面意義來說,你不是因為自己才這樣做,你不只是因為這是對的才這樣做,或者只是要安自己的良心,更不只是因為你有信心你的行動可以達成目的。你的反抗正是展現團結的作法。跟那些堅守原則及拒不服從的人們團結在一起:這裡、那裡、過去和未來。
抵抗做為一種團結
梭羅在1846年為了抗議美國對墨西哥的戰爭拒絕繳稅而入獄,但戰爭並沒有因而停止。然而,這個幾乎不算處罰的短暫監禁(在監獄待了一夜)卻引起了廣大的共鳴。它鼓舞了二十世紀後半一直到現在的各種抵抗不義的反抗行為。
在80年代後期,有一個運動要求關閉美國內華達州的核武測試場。這個場是當時美蘇核武競賽的一個關鍵地。這運動最後並沒有成功,測試場仍然照常運作。然而,這項運動卻直接促成了阿馬阿塔(Alma Ata,現今哈薩克共和國的一個城市)的反核運動,最後使得前蘇聯關閉位於現今哈薩克共和國(Kazakhstan)的主要核武測試場。這些抗議者表示他們受到內華達州反核運動者的鼓舞,於是決定以行動與居住在內華達測試場地上的美國原住民團結在一起。
你的反抗行為或許無法阻止不公義的發生,但這並不會使你卻步,因為你的作為是為了維護整個社群的利益。
因此,作為一個壓迫者並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因此,作為一個可以任意對任何一個國家施展其意志的超級強國,也並不符合美國的意志。
對一個現代社會來說,只有正義才符合了真正的利益。有系統地壓迫和限制你的鄰人不可能是對的;謀殺、驅逐、併吞、建築高牆等使得一整個民族陷入困境與絕望的行為,也不可能帶給壓迫者安全與和平。
美國的總統似乎相信他有權可以成為地球的總統,並且宣稱如果你不跟美國站在同一邊,就是跟恐怖份子站在一邊。這也都是不對的。
那些為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難與權益而積極英勇反抗以色列政府的以色列猶太人所保衛的是以色列的真正利益。我們這些反對現今美國政府的全球霸權計畫的人才是愛國者,我們的作為也正是為美國利益著想。
在這些值得我們熱切堅持的奮鬥之外,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謹記,在政治反抗的過程中,因果關係往往是間接,而且是錯綜複雜的。所有的奮鬥和所有的反抗都是真實具體的,而且它們也勢必如此。所有的奮鬥也都會有全球的影響效應。如果不是在這兒,就是在那兒,如果不是在此刻,就是在不久的將來。
獻給 大主教奧斯卡.羅米洛(Oscar Arnulfo Romero)。
獻給 若雪.柯利(Rachel Corrie)。
獻給 以夏.門努凊(Ishai Menuchin)以及他的伙伴。
蘇珊.桑塔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