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以往,美國出於石油利益介入中東,出於猶太人對美國的影響在經濟、軍事、道義上明顯偏袒以色列,大大增加了巴以問題的複雜性。如今,當布希為中東和平路線圖忙得不可開交之時,當巴以雙方的民眾和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再次把希冀和平的目光投向這項舉措之時,以色列一位享譽世界的作家以真實而深切的筆觸出版了自己10年中關於巴以衝突的文集。
1993年9月13日,在拉賓與阿拉法特簽定奧斯陸和平協定最終確立了一個和平框架之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似乎迎來了第一次和平談判的機會。人們同樣懷著和平的希望,僅僅幾年後這種謹慎樂觀的希望就讓路給了如今雙方暴力衝突的現實。在經歷了將近10年的痛苦與衝突後,這種希望已經消失殆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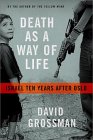
巴以衝突這非同尋常的10年被以生動的文字記錄在以色列知名作家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的新書《死亡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奧斯陸和平協定十年後的以色列》中,這是格羅斯曼從1993年至今發表的相關文章合集。這些文章使人不只從報紙和電視簡單的兩維空間的新聞中、從雙方政客的說辭中看巴以衝突,而且也從這些把死亡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人群內心深處去瞭解巴以衝突的實質。正如這本書的書名《死亡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所寓意的那樣,這是一齣人類歷史上最為荒謬的戲劇,雙方在一場近乎自殺滅絕式的衝突中,逐步走入越來越深的自我毀滅的深淵。
和平需要一種特殊的勇氣
 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
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
作為一名在以色列享有盛譽的作家,格羅斯曼曾出版了五部小說和兩部紀實作品。他在1987年創作的作品,《黃風》 (THE YELLOW WIND),一部反映巴以衝突的長篇紀實作品被翻譯成22種語言,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黃風》這部作品中,格羅斯曼以中東著名的六日戰爭為開頭,以真實的筆觸記錄了在約旦河西岸被佔領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世界通過他的眼睛,看到了在生死間掙扎的兒童,看到了慘死在槍下的大學生,聽到了巴以雙方普通民眾交流的聲音。
在格羅斯曼最新出版的《死亡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書中,我們再次跟隨這位以色列傑出作家及倡導和平的先驅者,去體會一個以色列人探索巴以和平的心路歷程。當1993年9月13日,當拉賓與阿拉法特握手,簽定了奧斯陸和平協定的時刻,格羅斯曼從心底歡呼著,他認為該協定可以使巴勒斯坦人回復「其自然的歷史進程中」,可以為雙方帶了和平的希望。他熱切地注視著巴以和平的進程,但是隨後日益加劇的自殺性炸彈襲擊、更加猛烈暴力衝突,使格羅斯曼最後不得不悲哀的宣稱巴以和平的希望已經死亡。
格羅斯曼在這本書中表達了自己對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衝突與戰爭根源的看法,他認為巴以之間衝突日趨加劇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於缺乏一種特殊的勇氣與精神。
格羅斯曼在文章中特別指出:他所指的勇氣和精神,並不是指某個人為了某項事業而犧牲生命,格羅斯曼特別指出:「解決巴以問題需要一種人類最為可貴的勇氣,那就是『當你身邊一次又一次發生自殺性炸彈襲擊,甚至當親人和朋友死於炸彈襲擊之時,以及當你看著自己的家園被毀,子彈無情地飛過之時,你仍然能夠繼續堅持和平的夢想的勇氣。這是一種特殊的勇氣,它需要敵對雙方,把對方看作是同樣懷著夢想與希望的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這種勇氣只有通過雙方真誠的對話才能實現。』」
理解與交流是和平的基礎
格羅斯曼在書中表達了對以色列更多的失望,在書中,格羅斯曼指出以色列人無法理解當巴勒斯坦人認為建立獨立國家的夢想越來越遙遠之時,他們只能更加絕望與憤怒。格羅斯曼認為,歷任以色列總理以及以色列人民的被動性已經背離了猶太民族的精神,把以色列變成了一個軍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日益倡狂的國度。在1998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格羅斯曼寫到:「600萬以色列人就這樣把他們的思想、意志以及判斷力屈從於某些利益集團,應該說他們是被動的犯罪,他們已經喪失了判斷是非的能力。而且也已經失去了那些能夠激起和提醒他們到底什麼是他們本來的目標與需要的本能,而這種本能恰恰對於作為一個社會與社會中的個體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在書中,格羅斯曼寫到:「即使是對中東最為漠不關心的人,恐怕也不會忘記一個名叫莫罕莫德-杜拉的12歲的巴勒斯坦男孩在巴以雙方交火中喪生的悲痛事件。」
2000年10月,格羅斯曼寫到:「據說是為了保護兒童,巴拉克和阿拉法特進行和平談判已經一年半了,但是顯然他們談論的只是某種抽象的和平而不是使成千上萬的兒童免於死在槍口下的和平。一個12歲的男孩如今正成為這兩者之間的犧牲品,這個男孩他切切實實地死了,我們能看到他弱小的身體,他死時驚恐的面容,而他決不僅只是一個名字,他是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兒童。假如巴拉克和阿拉法特能夠再勇敢一些,這個男孩也許就不會慘死在槍下。又有誰知道還會有多少無辜的人將在雙方的衝突中喪生?直到雙方能夠以這個死去的男孩生前的眼睛,這雙我們共同珍視的目光來看待這個世界,巴以雙方才能找尋到和平的軌道。」
巴勒斯坦人在格羅斯曼的筆下不再僅僅是一些名稱,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忍受著各種傷痛,他們有自己的需要正如以色列人一樣。格羅斯曼堅持認為以色列人應該去瞭解和理解巴勒斯坦人。在這本書中,你能看到格羅斯曼在電話中與他的巴勒斯坦朋友交談內容,他們彼此真誠地談父母,談教育也談政治。在書中,他寫到:「我的這些巴勒斯坦朋友們與我分享著共同的快樂,他們同樣認為以色列人並不只是一個民族的名稱,而是一些真實的,可觸及的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應該交流與理解。」
在格羅斯曼的書中,我們第一次聽到了來自這些真實的巴以綠色通道的談話,這些不是政客的說辭,不是新聞中兩維的簡單報導,而是巴勒斯坦普通人與以色列普通人之間坦誠的交談。他們談理想,談現實,他們談自殺性炸彈襲擊,談死去的大學生,談一個三歲流浪兒童的死等等。在字裏行間我們能夠看到一顆顆真誠的渴望和平的心靈。
巴以衝突是人類歷史上一齣最為荒誕的戲劇
但是和平似乎永遠藏在了人們的心底,而現實卻是更加殘酷。一次又一次失敗的和平會談,一次又一次的自殺性炸彈襲擊,一次又一次軍事行動似乎都在見證著格羅斯曼在書中的話語,「和平沒有希望」。格羅斯曼的深切的悲痛來自於感受到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走在同一條路上,但卻無法共處。
奧斯陸和平協定之後到底哪裡走錯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到底如何才能走向和平?無休止的暴力事件如何影響和改變著雙方的生活以及他們的精神?在行文之間,我們不只看到一個作家和記者對於巴以和平的精闢見解,同時我們也能感受到作為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以及一名和平主義者對於雙方領導人在和平進程中的失望。
自從奧斯陸和平協定簽定後的十幾年的進程在格羅斯曼的筆下是一場近乎荒謬的戲劇。在巴以衝突不斷的十幾年中,人們從希望走向失望,從可能走向不可能,從理智走向荒誕。在書中,格羅斯曼寫到當人們為以色列總理拉賓與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的歷史性握手而歡呼時,卻最終發現,他們手中握著的不是橄欖枝而是刀、槍、炸彈和坦克以及一切致命武器。正如這本書的書名《死亡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所寓意的那樣,這是一個近乎荒謬的邏輯。雙方在一場近乎自殺滅絕式的衝突中,逐步走入越來越深的自我毀滅的深淵。
在書中,格羅斯曼通過各種發生在周圍的軼事以生動的文字描寫了在自殺性爆炸不斷發生下的以色列人生活的剪影,為讀者展現出一個由於針對和平進程所表現出的不同意見衝突而陷入四分五裂的以色列社會。就在以色列前總理拉賓被刺殺之後,格羅斯曼寫到:「我看到一名男子走出他的汽車,迅速把原來貼在汽車後部的一個黑底紅字的標語『拉登是兇手』撕了下來。我想,如果他回家後,他如何向自己的孩子解釋呢?他如何向孩子們解釋在他走之前他的車上還貼著字條,可在拉賓遇刺的當天回家後,他就把字條撕掉了?」
格羅斯曼對於巴以衝突這種深入人們內心的探索,也體現在他對巴勒斯坦民眾對於自殺性把紮襲擊的看法上。在書中他寫到,在巴勒斯坦有很多人反對自殺性炸彈襲擊的方式對付以色列的暴力,並不僅僅是由於這種方式襲擊無辜平民造成的殘酷後果,而更多的是由於他們認識到:「假如一個社會已經習慣於把年輕的男女送上自殺襲擊無辜平民的道路,習慣於鼓勵這種行為並給予執行者以榮譽,那麼這個社會終將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而這種意識甚至在巴勒斯坦建國後也不會消失,當巴勒斯坦人為不同的政見而產生內部衝突之時,這種恐怖襲擊的手段將會掉轉矛頭指向國內事務,巴勒斯坦人已經看到這種手段對付強大的以色列是多麼有效,他們也會使用它來對付自己人。沒有任何特殊的情況能夠保護阿拉法特和阿巴斯不會同樣遭遇拉吉夫-甘地的命運,因為任何瞭解中東歷史和現狀的人都清楚,溫和派往往是極端主義分子襲擊的目標。」
格羅斯曼認為夏龍和阿拉法特對於巴以間衝突的加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寫到:「夏龍和阿拉法特都成功地煽動了暴力的火焰,煽動了彼此間的仇恨與暴力,他們成功地運用政治手段和宣傳機器使雙方的民眾認為這是他們選擇自己道路不可避免的結果。他們的行為以及如今的一舉一動都反映了他們各自好戰、相互猜疑以及好鬥的世界觀。對於他們來說,一切都是為了證明他們自己是多麼正確。而恰恰是他們應該受到譴責。」
格羅斯曼的思想的聲音第一次使我們意識到:在解決這樣一場人類之間最為致命的衝突中我們只能依靠我們人類特有的寶貴方式,這就是理解、交流、勇氣和信心。而剛剛對阿拉伯人投下炸彈後的布希政府,具備這樣的勇氣和信心嗎?多年來對中東和巴以問題日益複雜化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美國,能給浸透血淚的巴勒斯坦土地帶來一個美好的未來嗎?
延伸閱讀:誰殺死了穆罕默德‧杜拉?

